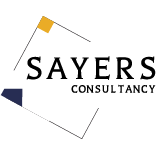1907年,毕加索之发现
二十世纪初,身处欧洲的艺术家们发现了新的艺术灵感源泉——非洲大陆。在1906年,安德烈·德朗(André Derain)参观了大英博物馆并被其中的面具与人像所折服。在写给马蒂斯(Henri Matisse)的书信里,他说他惊异于这些物品的原生表现力,并意识到艺术家们有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可运用。
一次神圣的邂逅
德朗与马蒂斯并不将这些面具与雕塑当作珍奇玩物,而是将它们看成是真正的艺术品,并且二人将这份狂热传递给了另一位艺术家——巴勃罗·毕加索(Pablo Picasso)。 虽然此后不久,毕加索的艺术作品便已然出现与非洲艺术相呼应的风格,但毕加索的艺术视野和他对自己画家身份的认知的根本性改变,是在他来年与非洲这些“神圣”且“有魔力”的艺术形式相遇之后才产生的。
1907年春,在德朗的迫切要求下,毕加索参观了巴黎的特罗卡德罗人种学博物馆(Musée d’Ethnographie du Trocadéro)。安德烈·马尔罗(André Malraux)在其著作《炼狱之镜-第二卷·绳与鼠》(Le Miroir des Limbes – II. La corde et les souris)中讲述了毕加索是如何描绘其参观非洲艺术品时的感受与启发的

毕加索写给马尔罗
“人们常常讨论非洲艺术对我的影响,我能说什么?我们都喜欢过物神偶像,如梵高所言,“每个人身上都具有日本艺术”。对我们而言,则是非洲艺术。它们的形态对我的影响并不比对马蒂斯或者对德朗的影响更大。只不过对他们两个人而言,那些面具与其他的雕塑并无不同。当马蒂斯向我展示他购置的第一个非洲人头雕塑时,他跟我谈及的竟是埃及艺术。
我去特罗卡德罗的时候,有种强烈的厌恶感,那里的气味如跳蚤市场一般。我独自一人,我想赶快逃离。但我没有。我留了下来。我驻足于此。我意识到这其实是很重要的。有些改变在我身上发生了,不是么?
这些面具并不能和所有其他雕塑相提并论。不,它们完全不同。这些面具是有魔力的。那么为什么埃及或迦勒底的物件没有魔力? 我们没能察觉。它们原始古旧,但并没有魔力! 这些非洲面具是代求者(intercesseurs),我是从这时开始才认识这个法语词的。它们抗驳一切; 抵抗未知与充满威胁的灵体。我一直注视着这些物神。我醍醐灌顶了: 同样,我也是抗驳一切的。同样,我也是认为一切皆未知,一切皆厉敌。整体的一切!不是细节——女人、儿童、野兽、烟草、嬉戏…… 而是整体的一切!我终于明白非洲雕塑是为何用。为何要以这样的方式雕刻、而非他法。毕竟,他们不是立体派艺术家!因为立体派艺术在那时还不存在。显然,一些人发明了一些模型,另一些人随之效法,这便是我们所谓的传统,不是么?但所有这些物神都是为同一件事效力。它们是武器。它们能帮助人们摆脱鬼魂幽灵的控制,帮助人们变得独立。它们是工具。若我们能给予灵体一个实体形态,我们便能够独立。灵体,潜意识(这一点还没太被探讨),情感,其实都一样。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何是个画家。
我在这惊悚的博物馆里孑然一身,在面具、印第安人偶、布满灰尘的人体模型当中。“亚维农少女”(Les Demoiselles d’Avignon)定然就是在这一天走入我的脑海中的,并不完全是因为形体构造,而是因为这是我的第一幅驱魔画,绝对是!”
安德烈·马尔罗,《炼狱之镜-第二卷·绳与鼠》,1976年。